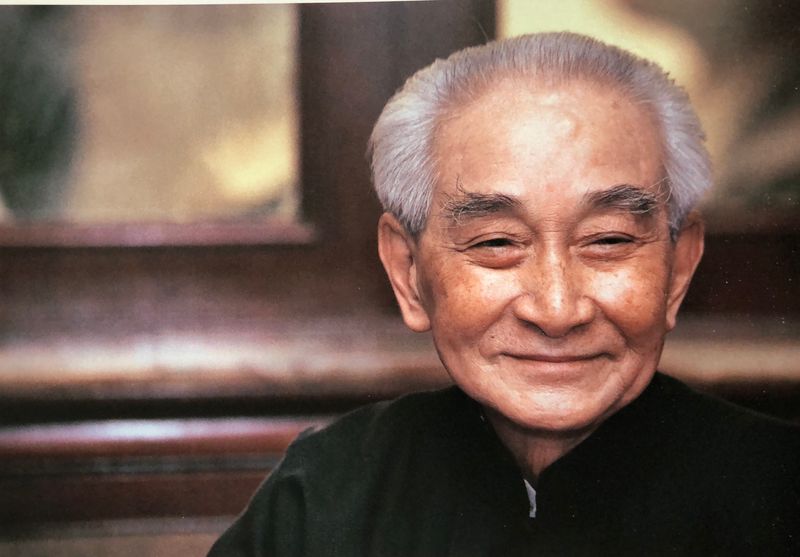
编者:本文转载自温州南怀瑾书院公众号。作者:叶正猛(温州学特约研究员、浙江省慈善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)。
引言:从一桩学术公案说起
十九世纪末,在中国传教、赈灾二十余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阿瑟・史密斯,却在其著作《中国人的性格》中断言:“慈善这种精神是中国人完全缺乏的”,宣称中国人行善皆为“积德求报”的实用目的,甚至主张以基督教作为救治中国社会的“药方”。
史密斯的论调提出不久,中国留美学生朱友渔的博士论文《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——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》,就给予正面回应与纠偏(史称“朱友渔命题”)。但是,史密斯的《中国人的性格》实在流布很广,他的上述观点仍留下不小的影响。
史密斯的这种指谪实则是对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误读,中国传统慈善动因并非史密斯所言,仅为“积福求报”。南怀瑾先生承袭“三教虽殊,劝善义一”的传统,倡导“仁之修养,佛之精神,道之高处”,其著作中丰厚的慈善论述,为我们进一步澄清史密斯的误读提供了钥匙。正如陈越光在《以公益为志业》中所言“慈善文化是慈善的成因和展现”,南怀瑾对慈善动因的诠说,正是南怀瑾解读传统慈善文化思想的基点。
南怀瑾对传统慈善动因的诠释
南怀瑾认为,人性是一个复杂问题。“几千年来都把形而下行为的性善性恶,扯到形而上的本体去讨论的,所以永远说不清。”(《孟子旁通》)因而,南怀瑾的传统慈善动因阐释建立在两大认知前提之上,这构成了其论述的逻辑起点。
其一,人与人的秉性存在差异。“一娘生九子,九子各不同”,即便是同父母所生,禀赋才智也迥然有别。南怀瑾援引佛学“种性”理论指出,这种差异并非单纯源于基因遗传,更源于个体自身带来的“种子”。例如尧舜是圣人,也是帝王,但尧的儿子不行,舜的爸爸不好,便印证了禀赋的独特性。(《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》)这种秉性差异决定了慈善动因的多元性。
其二,个体本身存在后天发展变化可能。《易经》的核心智慧在于“变”。南怀瑾在《易经系传别讲》中说:“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,没有不变的人,无一而不变,也不可能不变”。这种动态认知打破了“性善”“性恶”的绝对化争论,为后天修养转化慈善认知、催生慈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天性说 ——“绝大多数人是有不忍人之心的”
孟子提出“性善论”,经《三字经》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 的普及,成为中国大众的基本认知。南怀瑾在《孟子旁通》中对其进行了辩证“别裁”。
他指出孟子以“众人嗜味同于易牙”论证人性共通的逻辑缺陷,“话好像说得很武断”。南怀瑾也介绍了荀子的“性恶论”以及“性无善无不善论”。但南怀瑾还是正面肯定人性中的善良根基:“其实人性都是善良的,做错了事,立刻会脸红一下。”(《孟子旁通》)这种善良的起点,正如孟子所说人有“不忍人之心”——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”这种情感无关功利计算,既非为结交孩童父母,也非为博取乡党赞誉。(《孟子旁通》)
现在,人们看到慈善救助行为,都会随口说“恻隐之心人皆有之”。在南怀瑾看来,“不忍人之心”是人类慈善的共同源头。他说,儒家称其为“仁心”,佛教名之“慈悲心”,西方宗教唤作“爱心”。“虽然只有在名辞的涵义与解释内容上,意义略有深浅的差别,但是在为指出人性本有善良光明的一面,并无太大的差异。”(《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》)对绝大多数人来说,这种先天善性遵循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”的扩展路径,从对亲人的关切推及民众,再延伸至万物,构成慈善行为的自然起点。
修养说 ——“君子爱人以德”
善良是一种自发的爱,仁爱、慈善是一种自觉的爱。前者更多地发自先天的品性,而后者更多地出自后天的修养。
“道是要修得的”。《话说中庸》中说:“‘修道之谓教’的一句,说明学问修养之道,是要使它还归本净,而合于天然本性纯善之道的境界,这便是教化、教育的主旨。也就是我们平常习惯所说的,道是需要修才得的,所以才有‘修道’这个名词。”“儒、释、道三家,谈修养的学问,观念几乎完全相同。儒家主‘存心养性’,佛家主‘明心见性’,道家主‘修心炼性’”。
南怀瑾在《原本大学微言》中明确:“为社会、国家‘诚意’‘正心’做实事,泛爱众而亲仁,是‘真儒实学’的标准。”而修养正是达成这一标准的关键。
儒家为修养确立了根本方向: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,其中 “依于仁” 是核心 ——“有了爱心,爱人、爱物、爱社会、爱国家,扩而充之爱全天下。”(《论语别裁》)
范仲淹是南怀瑾推崇的有德性而行善的典范。他“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”,以千亩良田设立慈善产业,其义庄凭借“永久储备” 制度与完善规矩运行800余年。范仲淹“敦尚风节”的品格(《原本大学微言》)在他大量的慈善事业中彰显。
佛教也为修养提供了具体路径: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是学佛起步,而“修十善业道”是修行成就的基础(《花雨满天维摩说法》)。南怀瑾详解佛教“慈、悲、喜、舍”四无量心,将其视为修养的进阶指南:“慈无量心”予众生乐;“悲无量心”,拔众生苦;“喜无量心”,随众生喜;“舍无量心”,平等无执。四者层层递进,最终成就无私利他的慈善境界。我们把慈悲变成口头语,孔子讲仁义,道家老子讲:“我有三宝”,第一宝就是“慈”。(《禅与生命的认识》)
正如北平白云观楹联所言:“世间莫若修行好”(《金刚经说什么》)。慈善是从别人的困难中看到自己的责任。修养说就是情怀说,也是责任说。
积福说 ——“善恶报应观是中国文化的中心”
上述史密斯将中国慈善归结为“积福求报”,实则是以偏概全,但也要承认他确实“窥其一斑”。南怀瑾明确指出“积福”观念的存在,揭示其背后三教融合的复杂原因。“善恶报应观是中国文化的中心”(《易经系传别讲》),客观上成为许多古人行善的一个动因,对传统慈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中国传统报应观的核心源自《易经》: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”。南怀瑾指出,这种因果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根基,“教育、政治、道德皆建立其上”。(《易经系传别讲》)在《易经杂说》中他进一步阐述,《太上感应篇》中说“祸福无门,惟人自召。”福祸非由天命,而系于自身作为,这构成了一部分人相信天命而行善的基本逻辑。
儒、道、释三家都讲因果报应。南怀瑾在《论语别裁》中提到“君子有三畏”时说:“人要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,在背后,才可以使他上进向善。宗教也是这个作用。”儒家主张“天人感应”,以“留余庆”告诫世人积善积福;道家提出“承负说”,今人之善恶必留福祸后代,形成“前承后负”的循环;佛教则以“因缘业报” 强调个体承担果报,通过“三世轮回”给予道德奖惩的承诺。这些观念从正面说都给古人行善以激励。南怀瑾以“救蚁得状元”“埋蛇享宰相”的典故印证报应观的教化意义:宋庠以竹篾救蚁群,终得状元之荣;孙叔敖小时埋两头蛇除害,后官至楚相。
当然他本身十分赞同“非因报应方为善”,强调了行善的本质在于行为本身。
流芳说 ——“善不积,不足以成名。”
南怀瑾在多部著作中揭示,“流芳百世”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内心追求,也构成慈善的重要动因。南怀瑾对此持辩证态度:既认可名声对行善的激励作用,又倡导“为善无近名”的至高境界。
孔子所言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,道出了古代君子对名声的珍重,南怀瑾同时强调“好名要看什么名”—— 真正的美名必源于“仁”的实践:“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?”孔子说:‘善不积,不足以成名。”孟子亦言“仁则荣,不仁则辱”,将仁德与名誉直接关联。因而,成名与行善形成了逻辑关系。因而,南怀瑾并不否定褒扬善行的价值:“宣传某人一分好处为十分,能促使其达到标准。”(《药师经的济世观》)展现了对劝善实践的灵活认知。
传统社会形成了多元“谥法”体系以彰显善名:朝廷给予的 “官谥”,亲族门生所立的“私谥”,南怀瑾提出了“民间封谥”,即老百姓的口碑。这种评价机制成为“奖善惩恶”的无形力量,特别是“民间社会对善恶封神的公论,是谥法的另一面,值得重视。”(《禅宗与道家》)
诚然,南怀瑾更推崇儒释道“为善不求人知”的理念,在多部著作中引证儒道释三家的箴言:孔子答子张“不践迹,亦不入于室”,主张善行不留痕迹;老子“善行无辙迹”,强调高洁行善;庄子“为善无近名”,将无名行善奉为圭臬;佛教“三轮体空”,要求布施时忘却施者、受者与施事。
报恩说 ——“上报四重恩,下济三途苦。”
“报恩”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南怀瑾以“上报四重恩” 将其升华为慈善的核心动因之一(《禅与生命的认识》)。他在1987年留美期间所作“四恩未报客心惊”之诗,便蕴含着这份执念。
“四重恩”涵盖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王恩、三宝恩,儒家的根基是孝悌伦理。南怀瑾引述,有子言:“孝弟也者,其为人之本与。”儒家将仁爱追溯至血缘亲情,孝心是爱心的源头。《孝经》更将“孝”扩展至“大孝于天下”——民众的互相仁爱,为政者视百姓如父母,便是“仁政”的体现。这种由家及国的报恩情怀,自然催生对社会的慈善担当。
在《历史的经验》中说:“汉人崔瑗《座右铭》言:‘施人慎勿念,受施慎勿忘。’此立身之道也。”恩恩相报,在古代也成为了重要的慈善动因。南怀瑾用“结草衔环”两个著名的典故为比喻,肯定了知恩图报的美德。
古老的《诗经》中就有“投之以桃,报之以李”“无言不雠(酬),无德不报。惠于朋友,庶民小子”的朴素情感。报恩理念经民间传承形成文化共识: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,彰显着报大于施的道德价值。报恩的最高境界是“善之循环”—— 将个体恩情转化为对社会的爱心回报,使慈善成为跨越血缘的道德实践。
“利益说”——“既以与人己愈多”
有人为善是为了索求某种利益,这种动因虽然不高尚,但如果达到真正的慈善效用,适度的利益索求应该允许。南怀瑾在解读《易经》“利者,义之和也”时说:“这里的利,是两利,彼此间都有利,才够得上利。”并且十分肯定《易经》的“利物足以和义”的观点(《易经杂说》)。这就是要纠正“慈善纯粹利他”的绝对化认知,承认功利性需求在慈善实践中的客观存在。明清时期江南士绅捐赠粮食入义仓,可按捐额减免家人的兵役、徭役负担。这种“以善易利”的模式看似功利,却客观上充实了慈善储备。在《老子他说》 中说道:“‘既以为人己愈有,既以与人己愈多。’你真为人服务的话,付出越多,你自己则会越加富有。”揭示了利他与利己、给予与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。
愉悦说 ——“为善至乐,为善心开。”
“为善最乐”是中国流传千年的格言,南怀瑾以亲身体验印证其真实性:“真帮人解决大事,不仅精神愉快,身体都舒服,这是阳性的喜。”这种愉悦感并非浅层快感,而是“由内而外的永久不退的至乐”,是高层面的慈善动因。(《维摩诘的花雨满天》)
现代研究印证了这一认知:浙江大学苗青教授提出“慈善是保健品”,一项25年的研究显示,老年志愿者死亡风险降低 24.47%,因为慈善能缓解焦虑、增加社交、建立抗病信念。正如明末慈善家杨东明所说:“贫人以得袄为喜,余以贫人之喜而喜。”这与西方功利主义“慈善带来幸福快乐”的观点相通。南怀瑾更强调其精神超越性——这种快乐远超追求身体快感的其它方法,“有上善、上乐、上喜的境界,才算是福报的成就。”(《维摩诘的花雨满天》)
这种愉悦感形成正向激励,行善时的付出反而带来精神富足,这种富足又驱动更多善举,构成“行善—愉悦—再行善”的良性循环。南怀瑾说,这是“不期然的福报”,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。
南怀瑾传统慈善动因说的现实启示
南怀瑾的传统慈善动因说,构建了一个多元辩证的分析框架:天性是先天根基,修养是升华关键,积福是世俗引导,流芳是心理追求,报恩是情感纽带,利益是本能促动,愉悦是良性循环。传统慈善绝非单一的“积福求报”,而是复杂动因的多向启动。
人与人的秉性存在差异,人个体本身存在后天变化可能。南怀瑾的动因诠释,充分印证了他的“变易”观。“求利”和“求道”的多元是社会客观存在,“求利”到“求道”的跃迁是社会美好期许,正如《易经》所言“进德修业”“生生不息”。南怀瑾的传统慈善动因诠释对现实慈善具有深刻启示意义:
其一,崇尚好人表率:以“德范”激活慈善的价值标杆。撇开人性的抽象定义,任何社会都有道德高尚、品行优异的“好人”,他们在慈善动因上,如慈善家张謇所说那样:“迷信者谓积阴功,沽名者谓博虚誉,鄙人却无此意。”(《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》)济世利他,风高节亮。南怀瑾始终赞誉好人在慈善中的引领作用,他的题词“愿天常生好人,愿人常做好事”,表达了世上定有好人的认知。这一认知很大程度植根于中国传统“士”的仁义担当精神—— 以“先忧后乐”为志愿的精英群体,不仅是慈善资源的重要供给者,更是慈善理念的“精神旗手”。好人引领力在于“德范”。今天更要激活慈善的价值标杆作用,以好人自身的价值观传递慈善的“精神内核”。
其二,正视道德层次:以“包容”拓宽慈善的参与度。慈善动因的多样性,启示我们尊重道德的层次性。南怀瑾的慈善动因说,十分符合古人说的“遇上等人说性理,遇中等人说因果”的辩证观。行善动因自然存在差异,只要“最终指向利他”,不必强行用单一评判标准。启示我们当代慈善要有“包容心态”。只要没有出格的念头、非分的要求,不同动因都应被尊重。尊重道德层次,本质是承认人性的复杂性,以包容打破慈善的“道德绑架”,让不同认知、不同身份的人都能找到参与慈善的“切入点”,从而拓宽慈善的社会参与度。
其三,适从劝善多元:以“低门槛”搭建慈善的普惠平台。古人有“教人以善毋过高,当使其可从”的劝善原则(《菜根谭》),反对将慈善“神圣化、高端化”—— 慈善不应只是“富人的专利”,也不应只是“圣人的修行”,而应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实践。南怀瑾说:“刘备在临死的时候,吩咐他儿子两句话:‘毋以善小而不为,毋以恶小而为之。’……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,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,为了国家民族文化,这个观念还是绝对不可忽视的。”(《易经杂说》)要以“宽容劝善”观念,推动慈善普通化。让“人人可慈善、时时可慈善”成为可能。真正实现了慈善的“普惠价值”。
其四、强化实践本源:以“利他”回归慈善的核心本质。南怀瑾强调“行善本身就是报应”,直指慈善的“实践本源”。慈善的终极价值,不在于外在的回报(如名声、福报、利益),而在于“利他行为本身”:当一个人帮助他人解决困难时,不仅为受助者带来了实际福祉,更在自身心中结出“爱心”的果子,实现了“善念”的提升。这才是慈善最根本的“报应”。换言之,就是对慈善的价值评价,要从“盯”动机转向重效果。南怀瑾说“‘同归而殊途’。殊途,道路不同,每一个人的思想习惯,各有各的想法,最后归到什么?其理只有一个。”(《易经系传别讲》)“同归”于济世利他,允许有多种“殊途”;多种行善之“殊途”趋于利他之“同归”。
南怀瑾诗曰:“功勋富贵原余事,济世利他重实行。”慈善动因的诠释,最终要落脚于慈善事业的推动施行!
copyright © 2016-2019 All rights reserved. 版权所有 苏州市吴江区南怀瑾学术研究会
苏ICP备2022019425号-1 苏公网安备32050902102319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