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
本文源自东方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的《万里无云万里天——口述南怀瑾》,转载自温州南怀瑾书院公众号。

魏承思,祖籍浙江余姚,1951 年生于上海。华东师范大学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(UCLA)历史学硕士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。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,并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。90 年代起,先后担任香港《亚洲周刊》《明报》主笔、亚洲电视新闻总监、《成报》总编辑、台湾《商业周刊》专栏作家。现居香港,任香港佛学研究协会主席。
魏承思的人生多番转折、跌宕浮沉,与南怀瑾先生有着极为深厚的师生情谊。他们有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理想,并在太湖之畔,殚精竭虑地让理想“照进现实”。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!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
人生浮沉间,他是我的引导者
记:魏老师您好,很高兴认识您!今天,我们特别选择位于温州的南怀瑾书院与您连线。您以前到过温州吗?
魏:我到过温州,但已是 40 年前的事了,当时我还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学生。那时候,我潜心研究佛学。大二还是大三那年,我从杭州一路过来,来到温州江心寺考察学习。
记:我看过您的履历,曾在政府任职,也曾在高校任教,后又留洋学习,再返回香港从事媒体工作。然而无论人生怎么变动,您始终潜心研究佛学,而南怀瑾先生刚好是您佛学上的老师。您在佛学上的坚持,是否与南怀瑾先生有关?
魏:其实是很偶然,我是先学习佛学,后才接触到南怀瑾老师。他在佛学上的研究,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,我后来就一直跟随他学习了。我这一生中有很多很多的老师,而他是在佛学领域给了我最大影响的那位。我这一生也有很多转折之处,冥冥之中又与南怀瑾老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我可以结合我自身的经历,谈一下我和南怀瑾老师的人生交集。
我 1951 年出生在上海一户中产阶级家庭。我祖上是浙江余姚人,一直是乡里望族,后因时代变迁,家道中落。但祖母和父母对我的言传身教非常好,我正直的人格与好学精神,在小时候就培养成了。
我 21 岁那年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师资培训班,之后在一所中学任教。但我非常向往去读大学,于是在 1978 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,用 7 年的时间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。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点。当时我的志向是专心致志地走学术道路,梦想创立一个史学新学派。
1985 年,我研究生毕业,人生再次发生转折,我独立不羁的性格没办法忍受按部就班的人生轨迹。当时,上海市委宣传部向我招手,我遂弃文从政,供职于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。正逢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,我参与设计了上海文化发展蓝图,真是眼界大开,可大展宏图!我觉得自己正渐渐从书桌走向了社会,从政治的旁观者变成弄潮儿。
然而,谁都没办法料到之后的风云突变,仕途中止。重挫之下,我尝尽世态炎凉,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,价值观也开始瓦解和重构,下决心重回学术界。
重拾学术,需学贯中西。我在 40 岁那年,别妻离子,负笈异邦,进入了美国洛杉矶加大(UCLA)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。在那所世界级大师云集的百年高校里,我真正接触到西方文明,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突破。但是,那却是我的人生又一次的低谷,蹩脚的英文程度、窘迫的财务状况,把我逼进了前所未有的困境,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。
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1994 年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,我投身香港传媒界。从此,十多年间,我先后在多家杂志、报纸、电视、新媒体和出版社工作。这段经历让我得以纵横海峡两岸暨香港,广交三教九流,追踪天下风云变幻。
而我心心念念的仍是学术。我始终认为,传媒只是职业,而学术则是我毕生的事业。我在工作之余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社会学,2001 年,已到知天命之年,终于拿下博士学位。
2008 年,在财务相对自由之后,我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到太湖之滨跟随南怀瑾老师进修,重新系统学习佛学和中华传统文化,也陪伴了南老师的人生最后阶段。
回望过去几十年,我下过乡、教过书、当过官、留过洋、办过报、学过佛,人生可谓丰富多彩。而南怀瑾老师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名引导者。
记:您还记得和南怀瑾先生第一次接触吗?您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他?
魏:当然记得。我第一次知道南怀瑾这个人,是在 1980 年,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大三的时候,刚刚开始接触佛学,四处搜罗佛学经典。那年,香港的何泽霖老居士给我寄过来一批书,其中一本就是南怀瑾老师所著。书中观点非常新颖,恰好解答了当时我对于佛学的一些疑惑。而且作者引经据典,思维广博,很让人佩服。
我一看作者名字,是“南怀瑾”,还以为是位古人,因为从措辞、用典的风格上来看,都是古人的风格。极大的好奇心驱使我四方打听他,才了解到他是一名现代学者,便开始有意识地搜寻他的著作来学习。
第二次接触南怀瑾老师,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。有一位朋友向我介绍刘雨虹老师,说她代表南怀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洽谈,计划出版南怀瑾著作。我这才知道南怀瑾老师在香港定居。我向他们建议先出版南怀瑾老师的文化类著作,例如《论语别裁》等。后来,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,促使了南怀瑾老师著作的顺利出版。
第三次接触南怀瑾老师,是 1995 年左右,我第一次见到了他。1994 年,我从洛杉矶返回香港工作,我四处寻南怀瑾老师而未遇。后来,在一个“海归”聚会的场合,偶遇赵海英博士,她说可以带我去见南怀瑾老师,我真是喜出望外!那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,我到了香港坚尼地道南怀瑾老师的会客处,一房间的人都在那儿等候了。六点左右,一位仙风道骨的长者拄着手杖飘然而至,一袭长衫,满面春风。
他果然是我向往已久的南怀瑾。
那时候,我还有一点担心,不敢说出以往在政府工作的真实身份,怕引起误会,让海英介绍我是《世界经济导报》记者即可,哪知道那晚居然遇到了当年在上海相识的刘雨虹、陈定国夫妇,我的“真面目”马上被戳穿了。然而,老师并未对此介意,之后,他常常把这个插曲向台湾友人介绍。想来,这还真是佛家的不起分别心啊。
我至今还记得那晚在饭桌上的情景。当时,客人们出于对他的恭敬之心,谨言慎行,我因为生性豪放不拘,在酒酣之余放言高论。想必当晚海英是为我捏一把汗的。不料在我向南怀瑾老师告辞之时,他竟然说:“你是个有匪气的文人,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,今后随时上来吃饭聊天!”从此我就登堂入室,成了他饭桌上的“常委”,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去坚尼地道。
“人民公社”,是大千世界的缩影
记:这段经历听起来非常有趣。魏老师,那时候南怀瑾先生设在香港的“人民公社”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与事?
魏:那时候,“人民公社”主要由两拨人组成,一拨被称为“常委”,这是个“基本盘”,都是固定的一些人,大家经常碰面,我就是“常委”之一。另一拨则是不固定的访客,是来来往往于香港的社会名流,来拜访南怀瑾老师。
我是很受南怀瑾老师喜欢的一位“常委”。原因有三,一个是我跟他对话从不唯唯诺诺,我不把他当神,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,而他恰恰喜欢这一点;其二,我是浙江人,他讲话会带一点浙江口音,有些人可能会听不懂,而我都听得懂呀;其三,我学历史,很多历史的来龙去脉,我可以跟他畅所欲言、对答自如。
此外,南怀瑾老师滴酒不沾,大家在他那里很少饮酒,我却很喜欢把酒言欢,竟然被南怀瑾老师特许“酒权”,为饭桌增添生趣。他知道我好酒,在后来的日子里,经常会藏那么一两瓶好酒,留着在与我见面时送给我。有时候遇到一些好酒的客人,他会给我打电话,乐呵呵地喊上我去作陪。
在我印象里,南怀瑾老师的“人民公社”,是完全不同于官场的另一个世界,这里没有职务的尊卑之分,也没有利益的冲突交集,充满着坦诚和融洽。南怀瑾老师以其超俗的风范、深刻的思想、机智的语言,以他的人格魅力凝聚着大家。
在“人民公社”里,我们这些“常委”和他互相熟稔了,亲热得就像一家人,往往在送走客人之后,还会陪他聊一阵儿天,大家听他讲故事,说笑话。老人家说得高兴了,还会离座手舞足蹈地即兴表演!他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,他跟我们模仿那些民国时期的名人,那叫一个惟妙惟肖!我们常乐得拊掌大笑。
那时候,“人民公社”门户很松,三教九流,只要有熟人带路,一般就能上得他的饭桌。有两岸的文武官员,有银行家、艺术家、企业家;有小商人、名教授、大学生;有国民党,也有共产党;有美国的外交官、法国的汉学家、印度的金融家和韩国的和尚,也有江湖上的兄弟大哥……他是有教无类,对来客不起分别心,除了不太愿意见媒体——主要是不愿被媒体打乱平静的生活。
在饭桌上,南怀瑾老师对来客提出的各种问题,是有问必答,不厌其烦。有时候会引用一段先哲的话,有时候会背古人的诗词,往往一句话,意思就全在其中了。
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有一次,我带文学家刘再复去做客。南怀瑾老师问他最近在做什么,再复说在研究《红楼梦》,老人家随即说自己喜欢书里的诗词,便一首首地背起了《红楼梦》里的诗词来,又说更喜欢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诗,有豪气,居然一口气背诵了好几首冷僻的石达开诗词。
我还记得,当时宾客里有一名入境处官员林先生,他当时听了南怀瑾老师的话,为香港回归做了很大贡献,后来遇车祸成了残疾人。老师千方百计帮他寻医访药,每次林氏夫妇来做客,他都待之如上宾。南怀瑾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,从来不会忘记任何对民族、国家做过好事的人。
记:南怀瑾先生的“人民公社”是否也随着他后来的迁居一直保留下来?包括他后来在上海和江苏吴江时期?
魏:是,“人民公社”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。2002 年以后,南怀瑾老师常住上海,饭桌也就随他搬到了上海番禺路长发公寓的住所。2006 年,当他定居吴江庙港之后,他的饭桌自然又成为太湖大学堂的中心。而在吴江时期的“人民公社”又与香港时期有了很大不同。现在想来,也很是感慨!
吴江时期,南怀瑾老师年纪越来越大,想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,不得不有人把关。一般人也就不容易成为他的座上客了。除却从前的老学生,此时的来客非富即贵,却也不如香港时期的纯粹。有党政官员,有富商大款,有官二代、富二代、秘书帮,还有过来表演特异功能的。他们很少有真来寻师问道的,都过来问神通、问官运、问财路、问婚姻、问长寿,真是什么人都有啊!还有人慕名而来,扯上他合个影,就拿出去炫耀自己是“南怀瑾的弟子”,似乎精神境界就一下子能拔高好几个档次。
那时候,南老师很无奈,常说自己是“陪吃饭,陪聊天,陪笑脸”的“三陪老人”。但他总是以佛家的慈悲语、和善心、柔软语使来客生喜乐之心。
不过,南老师对客人也有非常严厉的时候。曾有几位银行的高层去见南老师,送他一套 18K 金雕刻的《心经》,然后说,准备以每套 3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市发行。
南老师非常严厉地说:“你们既然送来了,我不好拒绝。这里是一张 3 万元的支票,就算我买下来了。但你们用佛经来赚钱,将来是要背因果的!”事后,他说,违背教理戒律的行为必须指出来,我们绝不能用佛法去做人情。
我常觉“人民公社”就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,是人生百态的一个舞台,我在这个舞台上见证了人事的流转、时代的变迁,也见识了喜乐嗔怒的庞杂人性。
唯有“经史合参”,才能掌握国学精义
记:魏老师,曾有新闻报道,您与南怀瑾先生在香港期间朝夕相处了两年。那时候,您应当是在香港新闻单位供职吧?怎么有时间与南怀瑾先生朝夕相处?您觉得他在佛学方面有哪些非同一般的造诣?
魏:首先,我要纠正一点,这个新闻报道有误。囿于现实原因,我未曾与南怀瑾老师朝夕相处,所以有时候媒体报道不可轻信。那时候,我在香港《明报》主笔,每天下午三点进报馆,次日凌晨一两点下班,睡五六个小时就要起床。那时候,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,每个星期还要起一个大早赶赴沙田的中文大学去修博士课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怎么可能与南老师朝夕相处呢?我只是在每个周末准时去坚尼地道,去“人民公社”见老师。
但是,在香港工作的时候,我的确是在南老师的引领之下,真正走向了学佛的道路。我在大学期间就接触佛教,并潜心研究,也就是那时候接触到老师关于佛学的理论,这个你是知道的,但那时候我只是把佛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。虽然早年就出版了几本佛学著作,充其量也不过是“口头禅”。后来,我是在老师的引导之下,才开始进行佛门实修。
我长期受科学主义的浸润,对禅坐一类的佛门实修不以为然。又因为工作非常繁忙和辛苦,我常筋疲力尽,面容憔悴。1996 年春节前,南老师要赵海英通知我,大年初一去他的寓所“打禅七”,这可是极个别人士才享有的待遇啊!我那时候却不识趣地拒绝:“家有高堂稚子,已订好机票要回家过年。”后来有一天,南老师见我面色疲惫,又一次劝说我:“尽管你不信佛,打坐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,不妨一试。”
我那时就半信半疑地跟着大家学起禅坐来。坚持了大半年,果然有起色,虽然工作压力不减,但朋友再见面时都说我面色红润,判若两人。那时候,我就养成了打坐的习惯,每年春节也留在香港,跟随着南老师“打禅七”。但我那时候并未将此与学佛联系起来,只是纯粹当作一种养生之法。
1997 年,南怀瑾老师又一次把我叫去谈话,他说,我是个可造之才,要传我“心地法门”,说能把此法修成的人不多,望我持之以恒。他还说:“你十多年以后也许会出家。若如此,则必成一代大法师。”那时候,我没弄懂“心地法门”是怎么一回事,也没动过出家的念头。后来,在吴江期间,我将此事旧话重提,南老师听罢哈哈大笑。他说,当时见我仍将佛法当学问,想把我哄入佛门。且知道我功名心切,不这么忽悠我,我哪肯认真实修?所以,南老师实在是因材施教,根据个人不同的秉性根器,施以不同的诱导之法,真是煞费苦心!
2008 年,我跟随南老师去往吴江,协助他兴办太湖大学堂。那时候,我已真正走向佛门实修之路,并协助老师开办了太湖大学堂大型“禅七”。回想起我这一路上心路历程的转变,从不相信到尝试,到真正成为其间的参与者,进而回想到在此期间,南老师循序渐进的引导和其中的良苦用心,我的感激之情实在不知如何表达。
在跟随南怀瑾老师学佛的过程中,我的思维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我认为只有用他所提倡的“经史合参”的方式,才能学通学精、融会贯通,真正学懂中华传统文化,掌握中华文化的精义。
什么叫“经史合参”呢?以《孟子》的授学为例,所谓“经”,是《孟子》七篇的本经,所谓“史”,是指孟子所处的时代,如齐梁等国当时约略可知的史料。
我们除了《孟子》本经之外,还要配合战国时期相关的历史资料,来说明孟子存心济世的精神所在。所以说,教条式的死记硬背,总是让人存在着不是绝对信服的心理,的确是要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。
此外,西式教育是分门别类的,大多数是将人类文化知识硬生生分开,学某个专业,就等同于要成为专攻一门的专家。我们现在的分类也是如此,就算是学个历史专业,也有着古代史、现代史的区别,古代史还有着唐史、宋史、明史之类的划分,这样其实是不利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学习。用这种方式来学习传统文化,往往是支离破碎的。
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?南怀瑾老师说,中国在秦汉以前,儒、墨、道三家几乎涵盖了全部的文学思想,到六朝以后,换了一家,儒、佛、道三家成为文化主流。这三家说到底有什么泾渭分明的区别吗?其实,它们之间是相互杂糅的,这才构成了庞大的、极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。我以《史记》为例,这是一部史书,但又是一部不朽的文学作品,那些人物传记写得栩栩如生。它也可以看作一本哲学著作,内容上夹叙夹议,还有特别精到的作者观点与评论。而应用的观点,时而会偏向道家,时而又会是儒家思想,而儒、道之间又有交叉结合。
因此,一个人必须深入儒、佛、道三家学问,由博返约,融会贯通,才能掌握其中的精义。南怀瑾老师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门径,他不同于一般学者,他能出入于儒、佛、道之间。
所以跟着老师学佛学,是以能“博”“专”结合,这能给人极大的清醒感、透彻感,在学问上可谓是能举一反三,通一牵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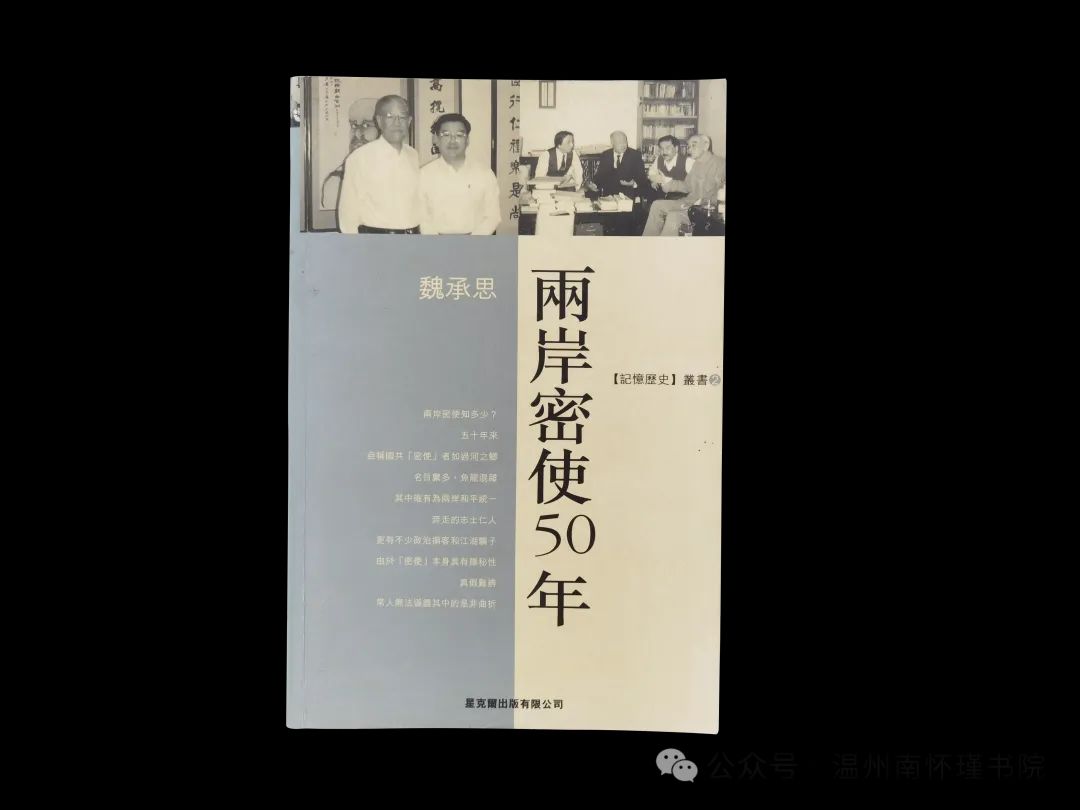
魏承思著《两岸密使 50 年》
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
记:魏老师,我知道您是《南怀瑾全集》前言的写作者,还写了一本《两岸密使 50 年》,讲述了南怀瑾先生在为两岸交流方面的贡献,可以介绍一下此书的创作背景吗?是不是也为了更好地传承南怀瑾先生的思想?
魏:2000 年,我的老友来新国先生和陈知涯将军打算出版《南怀瑾全集》。南老师指定我来写前言,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。动笔之前,最难的是如何给他定位。我最终定位老师为“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”。我想,这是我所写前言最大的意义之所在。
南老师一生行迹奇特,常情莫测。年少时即广泛涉猎经史子集,礼义具备,诗文皆精,并习各门派武术,毕业于浙江国术馆。早年钻研道家,青年时代发心学佛,遁迹峨眉山,在大坪寺闭关三年,遍阅《大藏经》。出关下山后,深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上师。
因而,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、易学大师,有人称他为佛学大师、禅宗大师、密宗大师,也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,但每一种说法都只涉及他学问人生中的一个侧面,他也从未以此自居。我曾经在文章中称其为“当代大隐”,如鬼谷子、陶渊明、孙思邈等,他们虽然对世事洞若观火,却宁可选择闲云野鹤的人生,而不愿出将入相,食官家俸禄,可是南老师并不认同这样一种人生定位。
后来想想也确实不妥,南怀瑾老师一生为续中国文化的命脉而奔波,到了台湾以后,担任文化大学、辅仁大学、政治大学等校教授,后又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、老古文化事业公司、十方书院等文化机构。1985 年,南老师离台赴美客居,直至 1988 年到香港定居。先后创办美国弗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、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、香港国际文化基金会等。前些年,更是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推广儿童诵读东西方经典的文化运动。
他的人生岂能用一个“隐”字概括?于是,在写序言之前,我花了半年多时间,将南老师已出版的所有著作重温一遍。温故知新,所得甚丰,准确地说,他应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。对于这样一个人生定位,老师是认可的。因此,当我据此写成上万字的《南怀瑾全集前言》送他审阅时,他一字未改地嘱咐送交付印。
如今南老师仙逝,任何学生若将他定义为一个“文化学者”、“国学大师”,或搞出“现代造神”运动,将他曲解为一个“宗教人士”的话,我认为都是对他的不敬。
事实上,南怀瑾老师一直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人。他名声极大,真正精通他思想的人却非常少,这么多年以来,他的学术、思想没有被总结过。大家都是瞎子摸象一样,摸到一部分,就说自己理解的那一部分。所以,那时候我很想系统地整理他的思想与贡献,出一本传记。而《两岸密使 50 年》的写作,原本是为了做老师的传记所整理出来的资料。
那时候,大陆与台湾尝试着恢复往来,有了彼此之间试探性的接触。南怀瑾老师成了其中的纽带、桥梁,他从中斡旋,做出了很多贡献。写《两岸密使 50 年》时,我认认真真地听了他与两岸来使沟通交流的所有录音,他晚年兴建金温铁路,为促使两岸对话交流出谋划策,为家乡故土的发展殚精竭虑……老师为国为民的情怀多次让我感动不已。
如果说《南怀瑾全集》及其序言是为传播他的思想,《两岸密使 50 年》则是想向众人展示一个真实、全面的南怀瑾。
记:听说在太湖大学堂筹建期间及其运营过程中,您是重要的参与者。那时候开办了哪些课程?南怀瑾先生给您哪些具体的指导,您有哪些成长和收获?我们都很好奇,在太湖之畔,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怎样的模式,如同星星之火一般传承开来?
魏:进入新世纪之后,南怀瑾老师很想在大陆找一个清净之地叶落归根。他始终认为,大陆才是传播国学的根源之地。
那时候,我们几个学生在杭州、苏州东山、上海淀山湖等地都看过好几块地,都不是很满意。那时候,老师归心似箭,一次去吴江庙港镇参观一位台湾老学生的工厂,看到太湖边风景如画,当场就拍板买下 300 亩滩涂地,计划在此造屋归隐,这就是后来的太湖大学堂。事实上,庙港那块地并不太适合居住,它属于滩涂地,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几经周折。直到 2006 年才初具规模。
大约在 2002 年至 2006 年那段时间,在太湖大学堂建成之前,南老师逐步迁居到上海。他一度邀请我去担任他的助手。2002 年年底,我正准备去香港《成报》出任总编辑。有一天,南老师把我叫了过去,他说,他打算回大陆定居,希望我与他一同回去。他还跟我讲:“我知道你要养家糊口,人家现在给你多少待遇,我就给你多少待遇。”
但那时我已签约《成报》,一批旧同事因我而准备“跳槽”去《成报》,南老师见我面有难色,不等我分辩就说:“你回去考虑三天,若不想回去,今后也就不必认我为师了。”回家后,我整整三天无法入睡,后来给老师写了一封传真,表示我确有难处。我说,师生名分既定,不想做专职秘书,变成雇佣关系。等将来有朝一日能卸下家庭负担,经济状况有所改善,一定前来侍奉左右,尽微薄之力。南老师见信后,让人转告我:“那就依你的意思吧!”
此后,南老师往来于香港和上海两地,渐渐在上海的日子愈长,在香港的时间愈短。大概一个月左右,我就会奔赴上海去看他一次。每到上海,我就在他的寓所边上找个小酒店住下,晚饭时,依然像以前那样陪他聊天。有人送南老师好酒,他就密藏在床底下,知道我要去了,就叫人拿出好酒准备。他在饭桌上总是跟大家说:“承思酒德酒品好,他可以畅饮,你们没资格像他那样喝酒的。”现在回想,那真是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。
2006 年前后,庙港那块地初具规模,南怀瑾老师决定从上海移居太湖之滨, 创办太湖大学堂。老师洞察世事,很有智慧,明确表示,太湖大学堂不是宗教场所,也不是教育机构、社会团体,只是私人闲居讲学场所。
在大学堂创办不久后,老师就问过我,如何规划这一块地?我当时拟了个草案,其中包括研究所、南怀瑾著作编译所、大讲堂、网上传统文化教学中心、海外汉学家进修中心。老师不置可否,却问我:“谁来做这些事呢?现在还有这么些能用的人才吗?”
这个问题触动了我,它迫使我去思考一些人才培养的方法。后来我跟他建议,我说我们这一代的国学都是半路出家,成不了气候,应该从小培养。不如效仿民国的无锡国专,在这里办一所国学专门学校,每年从贫困地区招收 20 名天资聪颖的失学儿童,学制 10 年,专教经史子集,10 年之后,这 200 名毕业生中,或许能有十多个成为真正的国学人才,传统文化自此薪火相传,不绝如缕。他们的生活费用,则可以由我们这些老学生认领。
老师对这个慈善与教育相结合的倡议非常赞成,派我去和苏州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商谈。朱市长听完整体设想后告诉我,想法不错,但不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,只教授国学的话,是违反九年制义务教育法规定的。于是这个设想也就放弃了。后来,办了吴江国际实验学校。该校在政府规定的教学大纲之外,又增加了一些国学内容。
2008 年夏天,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,来到吴江,在南老师身边常住,履行我当年的承诺。那段日子,生活很是悠闲平静。早晨在禅堂,下午读书,晚上听他讲经。我跟你说过,南老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,真的像个老顽童,常迸出很多新鲜有趣的念头。一会儿说,要养几头毛驴,和我各骑上一头,在湖堤上柳荫下溜达。
一会儿又说,在湖边建个亭子,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里赏月。他甚至在大学堂开了个咖啡馆,结果没多少顾客,都是他老人家掏钱请我们几个学生喝。
2008 年 9 月,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开学,首批接收了 29 名 5—9 岁的学童。南老师要我教他们《千字文》和《幼学琼林》,帮他们打好国学基础,他还亲自上了几堂示范课。学校教师的古文基础也不太好,我就又在放学后给教师和大学堂的员工们讲《古文观止》,大家都很有兴趣。没想到,后来慢慢促成了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,以及后来在太湖边的“禅修”。
有一天晚饭之后,南老师说,现在很多人想读佛经,但起码的古文基础都没有,怎么读佛经呢?不如办一个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。他让我领着大家学点古文,并当场指派斯米克老板李慈雄先生做班主任,负责办班的行政事务。
当年 12 月,讲习班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开学。南老师很是关切,怕我太学究气,学员们会听不下去,派了好几个大学堂的师兄弟来旁听。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打电话过来,询问课堂状况。直到我一口气讲了 8 个小时,学生们还不肯散场,老师才如释重负。
这个讲习班从此坚持了下来,每月一次,持续了一年。讲习班轰动一时,学员们从全国各地、四面八方赶过来,有深圳的、北京的,他们甚至坐飞机过来听课。这种对于国学的热忱让我很是感动。
我重回上海讲学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。到了 2009 年 6 月,复旦大学校友读书会和宗教研究所邀我去做一次讲演。那时候,我也很有一种“穿越感”,记忆一下子回到 20 年前的夏天。我告诉南老师,在 1989 年 6 月,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“禅与人生”的讲演,但那时候讲的是口头禅。如今有了一点实修的体会,还想以同样的题目再讲一次。南老师极力赞成,他还教了我一点讲课策略——他吟诵了唐人王播的诗:“二十年前此院游,木兰花发院新修。而今再到经行处,树老无花僧白头。”“上堂已了各西东,惭愧阇黎饭后钟。二十年来尘扑面,如今始得碧纱笼!”让我以此作开场白。
那次演讲完毕,听众们久久不愿散去,他们说有一个“禅学会”,还想来太湖大学堂跟着学禅修。我回去向南老师汇报,南老师说:“如果他们答应了三个条件:一、禅修七日每天坚持坐禅九枝香;二、七日内专心禅修,不准使用电脑手机和外界联系,不准脑子里还想着生意经;三、吃素七日,我就亲自带大家禅修。”我对复旦禅学会的负责人一说,他们当即表示愿意遵守。
9 月 13 日到 19 日,一百多人齐聚太湖大学堂学禅修。南老师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大家,打破日常起居时间,从早到晚在禅堂里。我们打坐时,他来回走动巡视,观察每个人的身体和神态变化,不断纠正大家的姿势;我们行香时,他手持香板在一旁注视,突然间一声香板站停,让大家体验刹那间的定境;我们休息时,他端坐于讲台上,给大家开示说法……一连七天,从无间断。这可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啊!
还记得禅修的头一天,南老师让大家先看了两段录像:一段是今日中国寺院里僧人禅修的画面:七扭八歪;另一段是现时日本寺院里僧人禅修画面:气宇轩昂。
对比之下,南老师说:“禅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如今东瀛邻国还保留着,难道在中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吗?”说到痛处,南老师老泪纵横,在场学员无不为之动容。这是老师最后一次主持禅修。
2010 年,国学导读班结束了。我和李慈雄兄建议再举办《管子》或《资治通鉴》的讲习班。最后,决定先讲《资治通鉴》,帮助学员们鉴古而知今。老师嘱我拟定办班计划,花三个月的时间,让学员读完六十六卷《秦汉纪》和八十一卷《唐纪》。
为了推进课程,我们把 100 多名学员分为 10 组,大家分头在家预习。4 月 10 日开班一天,5 月和 6 月各有三天在大学堂集中。上午小组讨论,下午全体集中交流,晚上老师答疑解惑。原先说好由南老师教授,我当助教。然而,南老师执意要加上我的名字,并由我主持集体讨论。我知道,他是有意赶鸭子上架,想让我慢慢接下大学堂的教学任务。我也不敢有怠慢,免得辜负了南老师的信任。
那时候,我每天十多个小时阅读《资治通鉴》,把每一卷的要点和思考题写下来,用电子邮件发给所有学员。南老师见状,一次次叮咛我要注意休息,不必过于认真,以免累坏了身体。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却不顾年迈,每逢集中讨论时就早早起身,在房间全程观看现场视频转播,及时补充阅读资料和思考题,晚上两个小时则亲自上台讲解。学生们怕他劳累,一遍遍地催他休息,南老师总是嫌讲话时间不够。那时的讲习班秉承南老师“经史合参”的学风,将儒释道的经典与历史记载比较、融会,来参究人生和社会的哲理。参与者曾用“震撼”两字形容此次学习历程。
人历长途倦老眼,事多失意怕深谈
记:南怀瑾先生是中华文化的弘扬者、传播者,在他的影响下,在你们这些学生的努力之下,国学日益兴盛,如今还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。2012 年南怀瑾先生的去世,让很多人悲痛不已。魏老师,您还记得与南怀瑾先生的最后一面吗?听说他在病中还在审阅您关于佛学的心得体会,给您留下过答复和批示。那时候,您在他身边吗?他给您留下的嘱托是什么?
魏:2010 年 5 月初,《资治通鉴》讲习班第二次集会前,我的右眼突然模糊起来。集会结束后,回到香港我就去眼科医院就诊。医生检查后告诉我是视网膜脱落,已严重到有失明危险,必须当天住院动手术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犹如五雷轰顶,眼睛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最宝贵的呀!一旦失明就意味着后半生再也不能读书写作了。
当我在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南老师时,听说他老人家心急如焚。手术后的 3 个月里,我遵从医生的嘱咐,不能运动和搭乘飞机,更不能看书了。白天只能耷拉着脑袋呆坐,夜里只能趴着睡觉。到了 6 月初,南老师说要取消讲习班的集会。而我执意要坐火车回大学堂主持最后一次集中讨论,让讲习班善始善终。在那三天里,南老师尽量让自己多讲,让我多休息。讲习班结束后,我回到了香港。手术似乎还算成功,但是后来右眼视力不断下降,现在只有 0.02。
8 月,我给南老师写了一封长信,想离开大学堂,留在香港养病。他当即回信,极表赞成。9 月初,我回大学堂去搬家。临行前,南老师把我叫到寝室中深谈。他说:“未来的两年里,你也许有一场大难。要躲过这场灾难,就在家一边养病,一边好好专修吧。想学佛要先学好做人,改善你自己的修为,尤其是要少造口业,再不要出口伤人。至于修行中遇到问题,今后可以和我书信问答。我的时日也无多了。在大陆学生中,你和我是感情最深的。我走后,大学堂也就散了。你就好自为之吧!今后出去弘法,不要学我。我年轻时曾经发愿,弘法不收供养。但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花钱的都以为不是好东西,不会认真听进去的。我自己学佛的路,是从《大宝积经》开始,由《楞严经》深入的。希望你循着我走过的路踏踏实实地前行。”
我泪水忍不住直淌。朝夕相处整整两年,听着他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那两年间,我觉得我学到最多的正是如何做人。做人要佛为心,道为骨,儒为表。其实,佛心就是一颗善心,对任何人慈悲为怀,不起分别心;道骨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清高风骨;儒表就是温良恭俭让的言谈举止。这些做人标准写在纸上,但现实中有几人能做到?而在我身边,就看到南老师这么一位圣人!
回家后的两年里,我把学佛变为生活重心,坚持每天拜佛、禅坐、诵经、念咒。十天半月给老师写一份学佛报告,汇报每天的修行中的感悟,提出种种疑惑和问题。老师总是及时回复,给我答疑解惑、鼓励和鞭策。我每过一两个月也会去大学堂拜望他。
2012 年 6 月 7 日到 9 日,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那三天内,他每天下午都在办公室给我开示修行中遇到的问题。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新著《〈瑜伽师地论 · 声闻地〉讲录》,要我回去认真研读,说书内讲的都是实修道理,对我有用。
他还鼓励我坚持修证佛法,将来可以直追欧阳竟无一班人:“因为你有他们的学识,他们不肯像你一样实修。”我便回答他说:“老师,你又在忽悠我了,是怕我放弃吗?无论如何,我还是会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的。”晚饭后,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坐在他旁边谈天说地。我原本以为,这样的情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,没想到竟是和恩师的最后一面……
8 月 13 日,我打算去大学堂,南老师让马秘书转告我:老师感冒,我去了他就要招呼我,希望这次不要去。我顿时觉得他这次一定病得不轻,因为 20 年来他没有一次不想我去看他。
8 月 16 日,我在报告中问他,读完了 12 遍《楞严经》,接下去应该读哪一部经。直到四天后,他在报告上最后一次批示:“最近气运不对,我也在维摩病中,深深业力之感,不可说不可说啊,无法与不知者言也。你从那年开始学佛,凭我深切的记忆,你真正发心想修行学佛,散散漫漫的还不到两年。承蒙信任,你恳切读《大宝积经》后,我希望你先能做到精读《楞严经》100 遍,希望在 10 年、20 年中贯通事理、证得真如,此话早已有所说明,只是你并不留意。我从青葱学道,身心投入出世修证法门,至今 95 岁,经常自惭暗顿,对于《楞伽》《楞严》二经,我从数十年身心投入求证的功力,尚不敢说是望及涯际。你这个话已经问过我三次以上,我都有所答复,或微笑而轻答,实际上语重心长,都已说得明白了。你如果对此有疑,今后 10 年、20 年中,希望你深入《华严经》《瑜伽师地论》二部大经论去吧。我老了,再没精力多说了,言尽于此,抱歉。”老师以前对我说话从未如此严厉过,最初我有点难受。我反复读了很多遍,才体会老师对我的拳拳之心,但只以为他是对我爱之深,责之切,没想到乃是最后遗言。
9 月 2 日,我写报告回复老师的批评,回顾了专修两年来的历程。5 日,老师请秘书回话:“现在四大违和,这篇报告要严重答复的,所以不要着急。慢慢来。”
但最后没有等来他老人家的片言只语。我的这一篇报告,老师会怎样答复?这真的是够我参一辈子的话头了。
还记得,老师走前最后吟诵的诗句是:“人历长途倦老眼,事多失意怕深谈。”他是带着对世事的无奈和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失望而西去的。
愿在浮躁的时代,激荡出思想的回声
记:魏老师,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。在您讲述的往事浮沉之间,我们深深感受到您与南怀瑾先生的师生情谊,以及你们执着于传统文化传承的赤子情怀。在南怀瑾先生去世之后,您是不是还一直在传承南怀瑾老师的思想、文化与精神,一直在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努力?
魏:2008 年之后,我在太湖之滨跟随南怀瑾老师静修,以及兴办太湖大学堂的那段时光,其实是我思想上逐步沉淀的一个过程。那时候,我重拾佛学和旧学,稍稍磨去了身上的狂傲、浮躁之气,也对现实政治的兴趣日益淡漠。从此之后,可谓“笑声骂声口号声声声刺耳,港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”。(大笑)
2012 年,在老师去世之后,我们依然坚持着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的课程。
2009 年至 2012 年,我们的讲习班讲完了《资治通鉴》,从 2012 年起,我逐步与上海复旦大学、上海浦东干部学院、同济大学合作,讲授“管子”“荀子”“中庸”等课程。随着课程的推进、时间的流逝,讲习班也如同大浪淘沙,渐渐留下了真正的国学爱好者、研习者,最后基本维持着 30—40 人的精干力量。他们真正地愿意跟着我学习,我也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影响,有好几个学生至今跟了我十几年了,他们在国学上的进步都非常大。
记:魏老师,后来还有关注吴江国际实验学校、太湖大学堂吗?不知道后来怎样了?
魏:我没有再关注过,或许你们可以去走动打听一下。之后世事变化莫测,整个社会人心浮躁,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兴趣再去系统了解国学,去研究南怀瑾老师的思想。现在社会上以南怀瑾弟子之名招摇撞骗者甚多,他们打着南怀瑾的旗号,干着为己营私的勾当,我冷眼旁观,只觉可笑。你不如去看看,凡是叫得最响,喊得最欢的所谓“南学弟子”,开着天价对外招生的所谓的南怀瑾传人,无一例外是沽名钓誉之徒。他们大肆宣扬自己对国学的热爱,你要真问他们一些国学的经典,半点都答不出来。我不屑与他们为伍,也不想去掺和他们的事。
我作为南老师的学生,我只想真正地,踏踏实实地传承一下老师的文化与思想。在 2020 年疫情期间,我在“喜马拉雅”APP 上开辟了《南怀瑾大学问 100 讲》,系统整理了南怀瑾人生经历与思想脉络,梳理了南怀瑾对国学经典的理解,发掘儒、佛、道学说里的文化价值、现代意义。我也撰写了一部新的作品《人生大学问:南怀瑾著作解读》,最近即将出版。如果有兴趣,你们都可以阅读一下,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南怀瑾,去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南怀瑾的著作。
人生七十古来稀。我已年逾七十,如今现代科技发达,物质生活富足,七十岁并不意味着生命已近终点。但恰似《新约 · 提摩太后书》所言——“那美好的仗,我已经打过了;该跑的路程,我已经跑尽了;当守的信仰,我已经持守了。”回望过往七十年,人生足够丰富多彩,已然无憾。接下来,我也想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,疫情过后,四处走走看看。尚有余力,再传承下中国传统文化,希望能在这个时代再碰撞出一些思想上的回声。
访谈时间:2021 年 12 月 23 日
访谈地点:温州南怀瑾书院连线香港
访谈记者:欧阳潇
copyright © 2016-2019 All rights reserved. 版权所有 苏州市吴江区南怀瑾学术研究会
苏ICP备2022019425号-1 苏公网安备32050902102319号
